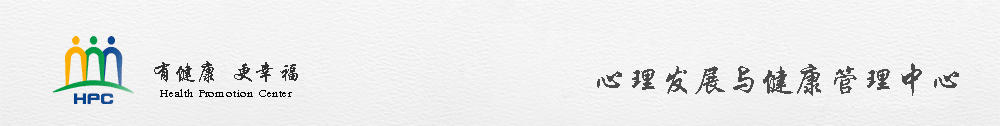2018年4月15日下午3点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第十二届文学节系列讲座之“原型与虚构:严歌苓的小说创作”对谈活动在逸夫第一报告厅顺利举办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,邀请著名作家严歌苓,《读库》主编、人大校友张立宪先生一同走进校园,就严歌苓小说创作中的“原型与虚构”问题展开对话。
 严歌苓畅谈多年写作的心得
严歌苓畅谈多年写作的心得
好作品要写出多重、朦胧的意义
一落座,严歌苓便打趣道:“张立宪和我就是原型与虚构,他的《读库》作为‘原型’给我的‘虚构’带来了很多启发。”对话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始。随后严歌苓以《红楼梦》与脂砚斋的点评为例,对“原型与虚构”问题作出了进一步阐发,并指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个尚未被发掘的面向,而小说创作则是把这一个面向放大为作品人物身上的某种主要特质。
以《小姨多鹤》为例,严歌苓说,“多鹤”的故事早已知道,关于日本遗孤,自己在中国方面、日本方面也都与真实人物接触过,做过采访,但是很久没有动笔。如果写一个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别,很容易写,亚洲人和亚洲人的差别非常难写,直到自己有一天到了日本一个小山村,住在很传统的日本的小酒店,看到日本老板娘铺床、擦地……发现她的背很有表现能力——传统的日本女人老是用背在跟你表现着什么,她的勤劳,她的那种含蓄,她的那种宁静,都好象是用背来表现的。从这个意上,忽然抓到日本女人的那种“气味”,于是才有了“多鹤”这个形象。为什么它不叫《母亲小寰》,为什么不叫《秘密家庭的秘密》,而是叫《小姨多鹤》,就是因为我找到日本人这样一个意象,就是一个敌人的女儿,她怎么被接受、跟她共存下来的故事。
“艺术就是艺术家带着他的性情诠释出来的真实。”严歌苓在这里借用左拉的名言,旨在说明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的所谓“真正的艺术”,其实是一种属于创作者的性情化之物。当被问及《小姨多鹤》从开始写作到完成所用时间时,严歌苓直言“写是很快的,但写之前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想‘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?这个作品诞生的价值是什么?’”她认为,一个故事的主题一定要是丰富的,而不能仅被单一阐释,小说的道德审美和艺术审美具有朦胧性,这样才具有了书写的意义。比如《小姨多鹤》如果只写反对战争之类,就没必要写。如果只是记录事实,那是报告文学,只有写出多重的、朦胧的意义,才是一部精彩的作品。“当年教写作课的老师就常跟我们说,全世界每天千万种书出来,你这本书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存在?你的生命是有限的,经历是有限的,创作的激情也是有限的,你要把它们给你认为最有价值去创作的东西。”
此外,严歌苓还指出同一主题,如果隔十年再写一次,可能就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面貌;但至少每一次书写都是当下最真实的感受,作品也就呈现为一种“让它发生”的自然状态。张立宪先生适时追问十年后是否准备再次书写“女兵”题材,严歌苓笑答:“我想不会了吧,脱下军装后的女兵倒是可以写一写。”
 严歌苓:最想写一部具有“抗拍性”的作品
严歌苓:最想写一部具有“抗拍性”的作品
最想写一部具有“抗拍性”的作品
严歌苓的作品大部分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,她自己本身也经常担任编剧的角色,更多人大约也是从这些作品中才熟知了严歌苓的名字。事实上,做为几乎与所有知名导演合作过的影视“红人”,严歌苓多年以来的愿望之一,就是写一部具有“抗拍性”的作品。《陆犯焉识》是严歌苓自认为重要的作品之一,也以为它有“抗拍性”,张艺谋的《归来》只是截取了它的片断进行了巧妙的改编。很多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,严歌苓笑称“太浪费时间,没看”,对谈在嘉宾与听众们的笑声与掌声中告一段落。张立宪打趣道:“原来你写了很多电视剧去耗费别人的时间。”对谈在嘉宾与听众们的笑声与掌声中告一段落。
随后,活动进入到提问环节,严歌苓针对同学们的踊跃提问一一作出耐心解答,点明“小说写得平淡没有关系,关键是把每一种感觉写得独一无二。”同时还强调了共感力、同理心以及倾听欲的重要性。
对于是否先有了明确的人物形象再开始创作的问题,严歌苓认为,人物的大致形象需要提前在脑海中留有一定印象,但其真正的性格却是在书写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。而当回答“大众传媒对文学作品最大的损耗”时,她指出“可能在于对汉语表达本身精准性的损耗”,并坦言“我觉得未来的小说不应该被完全影视化。”
此次对谈活动在热烈轻松的气氛中进入尾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