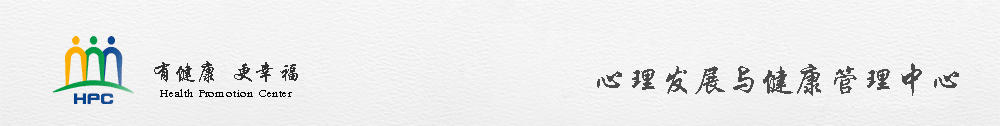2016年出版的张悦然的新作《茧》、葛亮《北鸢》几乎占据各种好书榜榜单,两本书都是历时七年完成,都是将目光投向父辈、祖辈的历史,看似不相关,却又有某种隐秘的相似,6月1日,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谈“遥望北鸢,时光成茧”在北大举行,张悦然与葛亮就关于写作、关于故乡、关于历史等话题展开了精彩的对话。
 《茧》 张悦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
《茧》 张悦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
《茧》:温柔新质地,文学新书写
张悦然的新作《茧》是2016年最受关注的长篇小说之一,它自出版以来迅速登上各大图书推荐榜单,入围深圳十大好书前50,荣获2016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赏(大陆场)“年度最期待作家”,并为作家赢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“2016年中国青年领袖”的荣誉。媒体和评论界也都给予这部作品高度的关注,并进行了广泛和深度的报道,为读者理解这部作品做了多方位的探讨。
张悦然是八零后非常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。在这部凝结了作者七年心力的作品中,张悦然用一种焕然的新姿重新面对广大读者,她带着自己的困惑与思考,用独属于她的那种灵动的语言,在历史的迷雾中穿行,张开一双八零后探寻的眼睛,为读者引领到一个历史与父辈的新场景中来。《茧》成功地跨越了作家青春经验写作的过往,而用更为素朴的写作直面一个成长的阴影。小说的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的童年是相似的,都在一团完全不知道的谜团中挣扎、突围,想要弄清楚无形中捆绑自己的是什么。张悦然借助两个人的双声部叙述,带领读者看见了他们彼此匮乏而又压抑的青春,同时也跟随他们窥探到父辈间纠葛的恩怨,从而触摸到了一个结了痂的历史的伤疤。这种探寻和把握历史父辈以及成长伤痕的写作姿态,在80后一代的作家中,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。
张悦然用一个跨越三代人,历时四十年的故事,既实现了自身创作上的蜕变,也让整个80后一代的写作掘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她让我们意识到,历史自有它的延伸和流转,历史是每一个个体的历史,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观察和思考历史的交接点。张悦然正是要借助《茧》来表达80后的立场和思考,为了要更充沛和温暖的今天,她决定来一次逆流而上的探寻。这是张悦然这部《茧》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的原因所在,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推广《茧》的意义所在,它的出版使人文社的作家队伍更加年轻化的同时,也让读者和评论者看到80后一代创作的更加成熟,这是文学创作梯级递进的良好发展态势,是大家乐见其成的成绩。
张悦然的《茧》,这部直接对话历史的创作,让我们在重新思考历史的血脉如何在几代人身上辗转流淌的同时,也开始重新认识观念意义上的八零后创作。我们相信,长篇小说《茧》不仅是张悦然个人创作的一座里程碑,也会是一部标志着八零后写作新质地和新方向的重要作品。
 《北鸢》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《北鸢》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《北鸢》:雅性见跌宕,磅礴见敦厚
《北鸢》是作者葛亮历时七年,首次追溯祖辈身世,以太舅公陈独秀、叔公邓稼先、祖父葛康俞等家族长辈的人生故事为部分原型,以商贾世家养子卢文笙的成长为主线,将波诡云谲的中国近代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,书写中国上世纪上半期丰盛起伏的断代。
政客、军阀、寓公、文人、商人、伶人,小说中上百位经典近现代人物,群落交织,进退沧桑,浑然磅礴。这些人物或风雅有致,或生性刚烈,或清明知礼,或隐忍智性,尽管时代风云翻涌,命运漂浮无着,可是人生一线,恰似风筝,人亦应有自己的主心骨。
上个世纪上半期,风起云涌,在重要的时代转型阶段,每个人都会面对时代的选择、内心的挑战。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文笙的成长为主线,叙写两个家族在半个世纪中的迭转与流徙。树欲静而风不止,如鸢而动,往复无际。因有一根主心骨在撑持,终归家有时。主人公文笙被卢家收养,开蒙、读书、于社会中立足、于安身中立命,岁月涓流,终汇成心底江河,“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” 。
作者用小说的虚构笔法叙写祖辈故事,朝夕观之,山水既成,淡笔浓情勾勒出二十世纪初波澜壮阔的社会全景,空间与时间跨度宏阔,人物群落众多,但是对于众多人物的把握自如、立体,生命力蓬勃,通篇故事脉络清晰顺畅,将跌宕的人生传奇喻于日常,笔触起落之间,入微而惊心动魄。
《北鸢》温润敦厚、正气充沛,字里行间,坐言起行,自始至终贯穿的是中国人的精气神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,了解来处,才知道自己的去向。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,命运漂浮无着。但一些“有文化传统的人”还总有“一线”在牵引,文化传统精神的时代意义在《北鸢》中力透纸背。在时代的动荡深处,也便可看清一些不变至永恒的东西,沉厚如静水。那关乎传统一脉,不随兴变而动,便是这个民族依存的底气。
《北鸢》从出版后就不断占据各大图书榜单,入选深圳读书月“年度十大好书”、 2016年《亚洲周刊》全球华文十大小说、 豆瓣年度中国文学第一名、 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优秀畅销书等多个榜单和奖项。央视2016年“中国好书”第一名,2016《人民日报》推荐30本书,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大媒体都对此书进行了详细的宣传报道,多家媒体、报刊杂志进行了长篇连载、联播,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。
真正的写作开始于异乡
张悦然、葛亮是多年的好友,而且现在的身份也都是高校的教师,两人不约而同谈到身处异乡时的“抽离感”给人带来书写故乡的冲动,葛亮说南京日常生活的舒服让人没有写作的冲动,但是到香港后,不同的文化对人的冲击,令人开始反思历史、反思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。张悦然则回忆起在新加坡读书的日子,“我最开始的写作、最开始的小说是在新加坡完成的,那时候会有一种情绪,一个是乡愁,再一个是有一种迷惘,对未来看不清楚,因为看不清楚产生对自我价值的怀疑,所以也是我开始写作的一个起点。”
做为城市中长大的一代,虽然年轻作家没有老一辈的乡土记忆,但这一代人有自己对“故乡”的记忆表达,同时随着年龄增长,这种记忆会在时间的沉淀中呈现出应有的底色,也标志着作家们告别青春的成熟。张悦然说,之前的写作并没有什么“故乡感”、内容也与童年的成长环境无关,“但是到最近几年,到写《茧》的时候,故乡开始在小说当中浮现出来,其实这是慢慢在记忆中复苏、慢慢在记忆中呈现的过程。对每个作家来说,当他过完童年的时候,其实他的经验已经足够了,已经足够支持一生的写作。”“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长的童年,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有同样分量的经验。在这点上我从来不会觉得因为欠缺某种乡村、欠缺某个大时代的记忆和经验,我的写作财富不够多。我会觉得我们不断的回溯童年,我们在童年中一个一个被关闭的匣子,会在未来的写作时间里面逐一被打开。其实我们所得到的馈赠并不比任何一代人少。”
葛亮也表示了相似的感受,“我们这一代人很天然的进入一个场域,这个场域是全球化的也是同质化的,在不同的城市,特别是大型城市,纽约也好,北京也好,我们发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趋同,作为小说作者就是要对这种趋同寻求一种逃避。具有乡土经验的前辈作家心灵深处有自己的原乡,这种原乡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要深入到历史记忆当中,也是在寻找这个原乡,这种原乡是逾越乡村的。在我们和父辈之间进行对话的时候,我们在寻找的是一个节点,这个节点是我们自己在当下的一种生存的意义。”
历史不是只属于一代人
关于写作经验,两位作家也有共同的感受和有趣的差异,张悦然的写作比较自由,《茧》虽然是从父亲那“偷来”的故事,但是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从来不干涉她的写作,也不曾过问她的写作情况。葛亮的《北鸢》来源于家族故事,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,关心葛亮笔下的再现,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,他深知需有自己的立场、见解乃至对历史的判断。同是耕耘七年的长篇,张悦然更喜欢日常的写作,“像练瑜伽一样,每天做一会儿功课”,而更加忙碌的葛亮平时更注重收集资料、做案头准备,写作主要放在有大段时间的暑假。
与关注现实、或以往的青春写作不同,这一代作家开始将目光延展到祖辈、父辈的生活,这无疑是作家的进步、同时也是更大的挑战。对于“非亲历者”如何书写历史,张悦然表示,历史不是只属于一代人,而是我们共同的历史。历史不是某种话语权,不是只属于一代人的财富。所以我们对过去的事产生兴趣,我们希望表达它、展现它,并不是“越界”的表现,因为这些都是和我们每天的生活、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都有关系的事情,我们要表达属于我们的思考。
葛亮说,“写《朱雀》时,我还非常羡慕这一代人,因为他们是历史的在场者,甚至是历史的记录者,而我们更多的是依赖想象的资源。但是在写《北鸢》的时候,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,我会开始要求自己变成一个历史的在场者。历史的细节就像工笔一样,需要一丝一扣的描摹,这种描摹的过程当中,对我自己而言意义也很大。我会觉得,当你真正进入到历史的记忆过程当中,你在演绎历史的时候,已经慢慢凝聚成你自己的史观。”
2017年的今天,两位文坛的新势力在北大举行文学对谈,是一次具有历史意味的对话。1917年,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,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由上海迁往北京,一个世纪前的文字激扬与文学改革,巧合的是葛亮的太舅公陈独秀正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创办人,这样一种血脉的流转在新一代文学青年的身上有了独特的传承。张悦然、葛亮所书写的故事囿于一个时代的逼仄、人心与生命的走向,他们所思考的是一代青年人面对历史的态度与诘问。在现阶段,他们通过《茧》《北鸢》完成了一次自我飞跃,在遥望中,破茧而出。